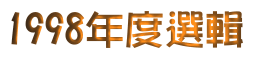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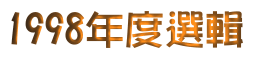
HPM隨筆(一)...................洪萬生03101998
HPM98馬賽行.....................洪萬生05261998
如何在課堂上使用數學史.......洪萬生10051998
負數的迷思.............唐書志11051998
誠如HPM所主張,數學史的確值得引進數學課堂之中,儘管它『如何』有助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仍然眾說紛紜,見仁見智。所謂HPM是指數學史與數學教學的關聯之國際研究群(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它隸屬於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ICMI,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專門推動數學史在數學教育上的應用工作。正因為如此,在數學課堂上運用數學史,就成了HPM成員十分關注的目標了。
根據多年來在很多場合 -- 包括台灣師大數學系所『數學史』課程、數學教師暑期進修班、數學教師短期講習班,以及應邀為初、高中數學教師演講 -- 討論HPM課題時,筆者總是再三強調在課堂上,教師運用數學史至少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1) 說故事,對學生的人格成長會有啟發作用;
2)
在歷史的脈絡中比較數學家所提供的不同方法,拓寬學生的視野,培養全方
位的認知能力與思考彈性;
3)
從歷史的角度注入數學知識活動的文化意義,在數學教育過程中實踐多元文
化關懷的理想。
至於運用之妙,當然存乎教師個人的慧心了。不過,筆者也一直被要求針對這些HPM課題,提供範本或手冊。本文之作,用在拋磚引玉,讀者萬勿照本宣科才是。
關於第一層次,很多人直覺地認為『數學史』就等於數學故事。不錯,教師說說故事提振學生的上課情緒,尤其是在夏日午後正好眠時,數學家或數學界的遺聞軼事,大概都可以達到提神醒腦的作用。在台灣師大就讀時曾修過『數學史』課程的教師,都一再向筆者表示她 / 他們的學生實在太愛聽故事了,簡直叫人窮於應付。事實上,數學家故事對學生的人格鼓舞與啟發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譬如說吧,十八世紀法國女數學家蘇菲 姬曼(Sophie Germain, 1776-1831),就是受到阿基米德(Archimedes)故事的『煽動』,迷上數學而終生無怨無悔。她童年時正值法國大革命發生,為了排遣難耐的孤獨與寂寞,遂被數學史家莫度西亞(J. E. Montucia)的【數學史】所記載的阿基米德傳奇所吸引。相傳阿基米德正沈醉在一道幾何問題時,對已經陷城的羅馬士兵渾然未覺,就莫名其妙被殺死了。這個悲劇讓百無聊賴的蘇菲神醉心痴,她想幾何學若真有這種魅力,那真地值得探索一番了。於是,她終於走上數學研究的不歸路了。
讓我們再提供另一個女數學家的故事。十九世紀俄國女數學家桑雅 卡巴列夫斯基(Sonya Kovalevsky, 1850-1891),多才多藝、文理兼美,在數學上她固然成就非凡,而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壇杜斯妥也夫司基、普希金等大師輩出的年代裡,在文學方面她也著作甚豐,頗富盛名,真是讓我們見識到數學家甚少為人所知的一面。同時,她雙方面的成就也告訴我們:原來數學研究與文學想像力並不相悖,而是正好可以相輔相成。事實上,正如桑雅的偉大師傅卡爾 外爾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 1815-1897 )的洞見:「傑出的數學家不可能不是心靈上的詩人」,數學與文學一樣,它是一門需要大量想像力的學問。針對她自己在數學與文學之間的隨意轉換,桑雅的自白是很值得轉述的:
至於這個故事應該如何『改編』,有請各自隨意斟酌。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啟發性的數學家故事(哪幾個方面?),值得喜歡說故事的教師善加利用。
就『說故事』的實施來說,教師有沒有一點從容的心情或『雅興』,絕對是主要關鍵。也就是說,教師只要平時喜歡閱讀數學家傳記,然後在課堂上多加練習,久而久之大概就可以出口成章了。這種『雅興』嚴格說來無關數學或數學史『素養』! 然而,如果我們希望教師在課堂上運用數學史時可以提升到第二層次,那麼,她 / 他們擁有一點數學史的專業修養,就變得不可或缺了。
筆者身為專業數學史家,為了強調上述這種HPM的特殊關懷不是所謂的『老王賣瓜』,在很多場合演講時,筆者總喜歡以畢氏定理的三個證法為例,來說明數學原典(或文本 text)上的記載,對學生的人格薰陶、認知啟發以及(多元)文化關懷,如何可以帶來深刻的影響。按照歷史順序,第一個方法當然必須是古希臘歐基里得(Euclid)【幾何原本】(The Elements)第一冊命題47,這即是所謂的『面積證法』,至於筆者所選擇的版本,則是徐光啟、利瑪竇(Matteo Ricci)所翻譯、出版的明刊本(1607年)(參考圖一)。第二個是古中國三國時代趙爽註解【周髀算經】所提供的『弦圖證法』(參考圖二)。第三個證法也出自【幾何原本】,是該書第六冊命題31。根據Proclus的說法,這才是歐基里得的原創性貢獻,由於它是關於相似形的定理(事實上,第六冊討論的題材都是相似形),它的的證法也因此運用了相似三角形的比例性質,於是被稱為『比例證法』。我們提供的圖形也是出自前述的明刊本(參考圖三)。
在簡介了這三種證法之後,筆者通常會要求聽眾(教師或學生)表態,請她 / 他們挑選一個最愛。結果,聽眾大都會表示最喜歡第二個證法,因為它比較直觀 -- 事實的確如此,但也可能是由於文化的親和力使然。接著,筆者會說明『數學證明』(mathematical proof)的功能,及其在教學、學習上應該扮演的角色。在這個前提下,筆者進一步督促聽眾『對比』這三個證法之間的異同,並強調它們在認知啟發上的重要性。
我們相信如果教師善用這種教學策略,學生一定有機會培養全方位的認識能力與思考彈性。至於真正的成效如何,當然還有待教育研究。不過,教師要想進行實驗,則起碼的數學文本解讀以及比較史學的初步修養,都是必要的數學史功夫,千萬馬虎不得。
另一方面,在第二個層次時,筆者已經刻意地鼓勵學生針對數學知識進行反省。一旦她
/
他們認為數學除了可以而且必須『做(或學著『做』)』之外,原來也可以『鑑賞』!
如此一來,教師或學生或有可能逐漸體會:數學是某脈絡中的一種知識活動(mathematics
in context),亦即它也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向度(或維度 dimension)。所以,學會了數學,不僅我們的生活經驗得以強化,同時,我們的文明品味也得以提升
--
尤其,我們也可以在這樣的教學設計中,分享世紀末最令人矚目的『多元文化關懷』。如果教師有機會與學生分享數學的文化意義,那麼,HPM的最終關懷乃至於數學教育的理想,也一定可以實現。這也正是我們上文所說的數學史運用的第三層次。有關這一方面的課題,我們可以論述得更深入一點,不過,這立刻會涉及更專門的數學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mathematics)或數學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mathematics),且讓我們以後再一一深入說明。
參考文獻
Fauvel, John and Jan van Maanen, "The Role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Discussion Document for an ICMI
Study (1997-2000)," Mathematics in School 26 (3): 10-11.
Furinghetti, Fulvi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Education, School Practice:
Case Studies in Linking Different
Domains," 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17 (1)
(February 1997): 55-61.
Kool, M., "Dust Cloud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Mathematics Gazette 76 (475): 90-96.
Osen, Lynn, 【女數學家列傳】(彭婉如、洪萬生中譯),九章出版社,1998。
![]()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到二十五日,筆者應邀前往法國馬賽的Luminy大學參加由HPM研究群(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所主辦的一個國際會議 -- "HPM Luminy Meeting"。會議場所設在法國數學會(SMF,Societe Mathematique de France)所屬的CIRM(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ncontres Mathematiques),緊鄰的是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所屬的一所教師研習中心。這個會議有來自三十個國家共七十位學者參加,目的是研商如何共同寫作這一本書 -- ICMI Study: The roles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athematics。本書預定公元2000年八月初第九屆國際數學教育會議(ICME-9)舉行前由Kluwer Publishing Co. 出版,希望可以為HPM的研究主題整合出一個規格(format)來。
更明確地說,這本書的功能是:1) 綜覽並且評價整個HPM學門的現況;2) 為教師、研究者以及涉及課程發展的專家學者提供資源與借鑒;3) 指出未來研究的方向與進路;4) 為那些打算在教學法中引進歷史的教育決策者提供指引與資訊。為此,John Fauvel(HPM上一任主席)及Jan van Maanen(HPM現任主席)特別在會前先草擬了本書的目次如下(括弧內的A's,B's 表示工作小組的代號):
Part 1 Political framework (A1)
Part 2 Cultural framework (B3)
Part 3 Student framework (A3, A4, A5, A6)
3.1 Research on classroom delivery of historical dimension (A3)
3.2 Research 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for trainee teachers (A4)
3.3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5)
3.4 Research on history for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6)
Part 4 Classroom framework (A2, B1, B2)
4.1 Analytical survey of ways of using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A2)
4.2 Detailed analysis and consideration of using original sources (B1)
4.3 Survey of historical support for particular topics (B2)
Part 5 Resource framework (B5, B6)
5.1 Non-standard resources (multimedia, instruments, www) (B5)
5.2 Bibliographical resources (B6)
每一位與會的七十位學者至少參加兩個工作小組,然後在長達五天的會議中,每個小組都各有10小時的熱烈討論,最後則分配工作。筆者參加了A2, B2的討論,最後當然也被分配了一個寫作題目,亦即:如何在課堂上引進畢氏定理的幾個不同數學傳統的證明,並說明它們的認知意義。
本次會議的特色之一,是提交會議的論文,多數在與會者赴馬賽前即已由主辦單位寄到。所以,與會者在第一天開會時,情緒就十分高昂,因為大家已經對自己與其他學者可能作出的貢獻了然於胸。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種場合,學術素養(譬如數學、數學史等等)表現最好而且態度最積極的,除了英國、法國、荷蘭的學者之外,也有一些來自數學小國(如希臘、丹麥、拉托維雅)的學者。譬如說吧,丹麥已退休的數學教育專家Tokil Heiede就展示一套該國的中學數學教科書,讓我們赫然發現數學史並非外加,而根本是數學內容的一部份 -- 其實該書主編正是丹麥頗富盛名的女數學史家Kirsti Andersen。當筆者請教Tokil Heiede萬一老師不能適應這種教材時怎麼辦?這樣的課程改革不是很基進(radical)嗎?Tokil Heiede回答得十分乾脆:"No, no, what do you mean by radical? It is a law!"
至於亞洲與會者中除了筆者外,有兩位來自日本(為ICME-9 2000 Tokyo作準備),有三位來自香港(蕭文強與他的兩位學生,馮振業與列治佳),以及一位來自中國的張奠宙(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ICMI的國家代表)。這幾位華人與筆者都是舊識,蕭文強是任教港大的專業數學家,在HPM的專題上頗有著述。張奠宙任教於上海華東師大數學系,除了關心數學教育外,對於中國現代數學史也頗有心得,他向筆者談及中國大陸的數學史家(包括一些在師範大學任教的教授)大都無瑕顧及HPM,言下不勝歔歔。
事實上,參加本次大會的專業數學史家除了Fauvel,van Maanen與筆者之外,就還包括了法國的Christian Houzel,德國的Hans Niels Jahnke與Gert Schubring等等。我們都相信數學史家在研讀典籍或文本(text)時,往往因為多了教育的關懷,而得以提出其他有趣的歷史問題。譬如說吧,從HPM觀點來進行Euclid對比劉徽的比較史學研究時,我們的確可以更具體地把握中國傳統數學的風格與精神。在數學教育的脈絡下考察華蘅芳(1833-1902)的【學算筆談】,我們也可讀出他在學習西算時,認知結構所經歷的挫折與掙扎。即以中國明代算學家唐順之、顧應祥無法理解宋元『天元術』為例,我們也可以因為現代學童對符號代數(symbolic algebra)的類似學習困擾,而賦以『同情的了解』,同時也對明代中國數學沒落的內在原因,多了一個觀照的角度。總之,HPM關懷對專業的數學史研究,絕對是積極且正面的(反之亦然),值得關心數學教育研究的學者專家好好地倡導與支持。這是1996年筆者前往葡萄牙參加HPM 96 Braga時,頗為成功分享的一個最重要的數學史研究心得。或許正是如此,Fauvel與van Maanen才會邀請筆者負責承辦HPM 2000 Taipei。
此次馬賽HPM,筆者原來並不打算參加,Fauvel與van Maanen也因為體諒筆者家庭變故,而不敢相擾。直到筆者聲明仍然願意承擔HPM 2000 Taipei研討會的任務時,才積極遊說筆者務必前往,以便進一步商量研討會細節。我們初步決定HPM 2000 Taipei將於公元2000年八月9-14日在台灣師範大學舉行,主題如下:
1) History of Asian and Pacific mathematics
2) Mathematics education before 1800
3) The effectiveness of history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empirical
studies
4) East and West, contrast and transfer of mathematical ideas
5) The recommendations made in the ICMI–Study Book
屆時預計有一兩百位各國學者與會,我們很希望國內也有數目相當的學者、專家及中小學教師參加,好好地展現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實力。
基於此,筆者期待國科會與教育部在未來幾年內大力支持HPM及其相關議題(譬如科學史與科學教育之關聯)的研究。到時候只要我們端得出『豐盛的菜單』來,不怕我們主導不了HPM相關議題的品味。其實只要有心,在國際學界的發言位置也不是那麼遙不可及,當然,將台灣的學術研究國際化,絕對是先決條件。有志之士,盍興乎來!
參考文獻
Fauvel, John et al., 1997. "The Role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Discussion for an ICMI Study (1997-2000),"
BSHM Newsletter 33: 46-53.
Horng, Wann-Sheng 1993. "Hua Hengfang (1833-1902) and His Notebook on Learning
Mathematics -- Xue Suan Bi
Tan,"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 Taiwanese
Journal 2(2): 27-76.
Horng, Wann-Sheng, "Euclid versus Liu Hui: A pedagogical reflection," to appear
in Victor Katz ed., Using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Washington: MAA.
洪萬生 1996. 『數學史與代數學習』,【科學月刊】27 (7): 560-567。
![]()
如何在課堂上使用數學史?
當同事問Kool如何在數學課堂上使用數學史時,她回答說:
基於同樣的考慮,當我在很多場合 -- 包括本系所『數學史』課程、短期數學教師講習班,以及針對初、高中數學教師與學生的演講 -- 討論數學史如何關聯數學 教育(HPM)時,我總是喜歡舉畢氏定理(the Theorem of Pythagoras)的三個證法 為例,來說明數學原典(或文本)上的記載,對學生的人格薰陶、認知啟發以及(多元)文化關懷,如何可以帶來深刻的影響。 按照歷史順序,第一個方法當然必 須是古希臘歐幾里得(Euclid)【幾何原本】(The Elements)第一冊命題47,這即 是所謂的『面積證法』,至於我選擇的版本,則是徐光啟、利瑪竇(Matteo Ricci) 所出版的明刊本(1607年)。第二個是古中國三國時代趙爽註解【周髀算經】時, 所提供的『弦圖證法』。第三個也是歐幾里得所貢獻,記載在【幾何原本】第六冊 命題31,由於它的證法運用了相似三角形的比例性質,因此被稱為『比例證法』。Do not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your classroom, but do it, use it!! Us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your teaching for reasons of variety and to give your pupils something extra! The extras that historical problems bring to your pupils are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mathematical insights. Historical problems may intervene at the end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as an extra exercise or the application of a new learned mathematical topic, or at the beginning to stimulate pupils to develop their own individual strategies.
在簡述了這三種證法之後,我會進一步督促『閱聽人』(audience,讀者/作者) 對比(contrast)它們之間的『差異』,並一再強調數學鑑賞之所由出。試想數學一旦被認為除了可以而且必須『做』(或學著『做』)之外,原來也可以『欣賞』。 如此一來,教師與學生或有可能逐漸體會數學是某脈絡中一種知識活動(mathematics in context),它也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向度(或維度,dimension)。因此,學會了它,不僅我們的生活經驗得以強化,同時,我們的文明品味也得以提升 -- 尤其,我們也可以在這樣的教學設計中,分享世紀末最令人矚目的『多元文化關懷』。
參考文獻
Furinghetti, Fulvi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Education, School Practice: Case Studies in
Linking Different Domains," 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17, 1 (February 1997), 55-61.Kool, M., "Dust Cloud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Mathematics Gazette v. 76, n. 475 (1992), 90-96.
負數迷思
台北市百齡中學 唐書至老師
如果抽掉國中課本裡的負數,老師們將會同意今天看來漂亮完整的公式都會顯得支離破碎;不論是討論數學裡的一元二次方程式還是物理學的運動方程式,沒有了負數便左支右絀,無以為繼。
也正因為負數大量出現在教材的各個角落,教師往往注意的是負數的運算性質,對於負數的認知卻著墨無多。什麼數字竟然會比
0還小呢?為什麼要說一個遞減的等差數列有負公差呢?甚至於這個恆等式(a-b)(c-d)=ac-ad-bc+bd又是怎麼算出來的呢?對於這一類問題,以往的觀點是認為一個「會教的」數學老師「必定」可以講得讓學生明白,而「會教」的定義往往取決於脈絡是否簡明、合乎數學的內在架構。 兩百年的困惑然而18世紀法國作家Stendhal(1783-1843)對於老師「負負得正」的解釋顯然並不滿意。他回想從前學習負數的情況:
數學是不會矯柔造作的。在我的青春歲月裡,我相信那些使用數學做為工具的科學也必然同樣真確;別人這麼告訴我。但是當我發現沒有人能解釋負負得正(-×-=+)的原因時,你能想像我的感受嗎!(而這還是所謂「代數」的一項基本規則哩。)對我來說,這個沒有解釋的難題真是夠糟的了(它既然能導致正確的結果,無疑地也應該可以解釋)。而更糟的是,有人用那些顯然對自己都不清不楚的理由來對我講解。
他的老師顯然不能理解學生對於「負負得正」的抗拒,無論如何解釋,總是不能讓
Stendhal信服;最後,只好搬出數學權威Euler(1707-1783)與Lagrange(1736-1813):他們知道的也不比你多多少呀,可是都用得理所當然,你又何必鑽牛角尖呢?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知道:
M. Chabert根本不曾聽進我對於負負得正的抗拒,M. Dupuy則老用縹緲的微笑回應,而那些我所請教的數學專家們總是報以嘲諷。我最後告訴自己:本來就必須負負得正嘛;畢竟,這個規則已經用了這麼久,而且導出的結果看來都無懈可擊。
或許是後來很多場合都用得到吧!Stendhal被這個問題(負負得正)困擾許久,最後只好接受它;然而這個學習經驗卻使他感受深刻,一度還動搖了對於數學與數學教師的信心。
我摯愛的數學難道是個黑盒子嗎?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到達真理;噢!那時是多麼熱切地想在邏輯或文藝上面吸收各種接近真理的方法啊!最終我以我可憐的、卑微的智力做出結論:
M. Dupuy可能在說謊;而M. Chabert則是一個自我欺騙的可憐蟲,完全不能理解旁人的抗拒心理。……我就教於d'Alembert在百科全書(Encyclopedia)中的數學文章,但他們自大的語氣以及對真理的傲慢卻令我排斥厭惡;而且,我對它們一點也不能瞭解。
從這段描述可以想見當時的Stendhal是多麼渴望求得心中疑惑的解答啊。時至今日,筆者猶記得班上同學拿著「(-5)+3」四處問人,甚至放學跑來問老師的可憐眼神;雖然做是會做了,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她的彆扭與不安。時隔二百年,古今中外仍同樣有孩子為了讓自己接受負數的運算規則而困擾。
對於Stendhal,數學這個黑盒子確實隱藏了太多,連大數學家d'Alembert(1717-1783)都不得不拐彎抹角地陳述自己所認知的「負」概念哩:
負量與正量對合
(The negative magnitudes are the counterpart of the positive ones)。負量始於正量所止之處。參見「正」條。人們必須承認,要正確地勾畫負數
(negative number)的想法並不容易;有的學者只是將他們不嚴密的說法加諸紛亂之上;說負數小於一無所有(negative numbers are below nothing)就如同在講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為了使牽涉負量
(negative magnitude)的代數運算能夠嚴謹與簡潔,人們傾向於相信與負量有關的正確想法必須簡單而且並非人造。假使人們想要展現此一真確概念,則須注意那被稱做負的、被誤認為在零的那一邊的量,常常是用真實量(real magnitude)表徵。這裡有個幾何學的例子,負直線與正直線的差異在於它們相對於某共同點上已知直線的位置。參見「曲線」條。由此可見計算(calculus)中所遇到的負數量(negative quantities)確是真實量(real magnitude)無誤。但是這些真實量必須賦予一種想法以有別於被接受者,例如:我們想找一個數字x的值,使之加100等於50。根據代數規則,可以列x+100=50,得到x= -50。這表示x的量(magnitude)是50,不過對100來說是減而不是加。也就是這個問題可以重新考慮如下:找某量x使100減之剩餘50。如果問題真這麼寫,則可列式100-x=50,x=50,x的負形式將不存在。因此,負量確實表示假設置錯情境之正量。加諸量前之"-"號乃是做為消去運算以及修正假設中錯誤之提醒,一如前述例題。參見「方程式」條。請注意此處所提及的只是諸如
-a或a-b(b大於a)之孤立負量(isolated negative magnitude)。如果a-b是正的,換句話說,b小於a,則符號無論如何不會產生困難。換言之,孤立負量並不存在於真實與絕對感覺
(real and absolute sense)之中;抽象來說,-3對於心靈沒有意義;當我說某人給另一個人-3馬克(thaler)時,才意味著他從另一個人身上拿走了3馬克。……就現在的情況看來,要進一步發展這個想法是不可能的,不過這卻是一個簡潔得無可取代的方式;我相信,我能保證它對於所有牽涉到負量的可解問題都不會出錯。……
請注意
d'Alembert提到「負數」與「負量」的不同態度。對他們而言,負數是一個「莫名其妙」的數,早在Pascal(1623-1662)與Descartes(1596-1650)的時代就這麼覺得了;Descartes認為負根是方程式中錯誤的根,而Pascal則認為要從「一無所有」當中減去東西,更是門兒都沒有!所以d'Alembert必須賦予已經展現許多用處的「負量」一些額外意義;如同他所說的,「我相信,我能保證它對於所有牽涉到負量的可解問題都不會出錯」,但他也同樣認為「就現在的情況看來,要進一步發展這個想法是不可能的」。倘使一直堅持從現實量的角度去理解,Stendhal終究要遇到這個不可解的困境:M. Chabert[被Stendhal問到]沒有辦法的時候,曾經不太恰當地強調,要我們將負數量看成某人的欠債。可是這個人該怎麼把10000法朗的債與500法朗的債乘在一起,好得到5000000─也就是五百萬法朗─的收入呢?
這,不合宜或不顯明的比喻
(metaphor),或許也是我們老覺得課本上(不論哪一種版本)「負負相乘」的例題奇怪的原因吧。 另類觀點除非觀點有所轉變,否則似乎難有更進一步的想法出現。果然,19世紀的數學家們經由形式上的探討,對於負數有了新的看法。以往來自量的束縛不再存在,當時H. Hankel這麼寫道:
要建構普適性算術的環境,必須脫離直覺,將數學當做純粹智慧與形式的產物。它並非量與數的合成,而是具有思維特性的實體
(intellectual object);存在於現實的東西與關係對應得到,但並非必要。
從此以後,似乎再也沒有必要去為數系找尋自然界的實例和比喻了;新數字不再被視為「發現」,而是被看成「發明」。這並非表示Hankel等人不關心數系與真實世界的連結,他們仍舊規定形式運算不能導致矛盾;一個免於矛盾的定義才是邏輯上可行(logically possible)的;同時,單只有邏輯上一致的規則還不夠,如果不將系統內容的詮釋與應用考慮在內,這些系統放在一起也是毫無意義的。透過「不變原則(principles of permanence)」,保持一些特定的規則不變,賦予適當的定義,得以建構出負數的「形式化」面貌。例如:一開始先「定義」負數-n是從方程式x+n=0的解而來,其中n為自然數;同時假定加法與乘法的結合律、交換律成立,分配律也成立(根據「不變原則」),於是可以進行論證。
(-3)+3=0
(-4)+4=0
∴[(-3)+(-4)]+[3+4]=0(前兩式相加的結果)
∴(-3)+(-4)=-7(因為3+4=7,再套用負數的「定義」)
那麼乘法是否也可以如此定義呢?從0×x=x×0(成立)開始,
[(-3)+3]×4=0×4=0,i.e. (-3)×4+3×4=0
[(-4)+4]×(-3)=0×(-3)=0,i.e. (-3)×(-4)+(-3)×4=0
根據定義,可以得到(-3)×4=-12,(-3)×(-4)=12(似乎有負正得到負、負負得到正的影子)。當然,這些只是大概罷了,嚴密的論證還需要一些充份的準備。(這個時候,有沒有嗅到本世紀中「新數學」運動的一點味道了呢?)
中國的負數概念又是一條不同的路。根據李繼閔的說法,負數之所以很早為中算家所引進,乃是由於古代傳統數學中,「算法」高度發達和籌算「機械化」的成果。劉徽在《九章算術》的注文中提到:「今兩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負以明之」,所以負數在中國古代是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概念,人們可以透過算籌的「正負術」推演解題;李繼閔指出,有些題目(例如方程章第三問)要不是因為籌算的緣故,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不必引入「負數」就可以解出答案。
單從這些例子,我們就看到完全不同於先前具體取向的兩種負數經驗:一個是西方的形式主義,一個是東方的籌算文化。漸漸地,西方部份數學家還瞭解到,負數的「相對」意義不見得非丟開不可;幾何的坐標化、向量的引介,以及負的電量、負的速度、負力……等等,往往因負數而使人類開展更廣闊的思考空間。人們不再將擴充數系的「正當性」訴諸現實,而是反過來,利用數去描繪現實情境與各種量。使用負數讓我們可以更有效率地解題:當代數學史家Wagenschein便說:「負數的運算法則是一種發明,但是卻是一種很好用的發明」。
非結論
不管以哪一種方式看待負數,今天都會運用它做很多事。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究竟是採取什麼樣的觀點面對負數呢?會像Stendhal一樣凡事去生活中找對應意義嗎?還是像d'Alembert一樣賦予「運算」額外的解釋呢?是像劉徽一樣把焦點放在「算法」上?還是像Hankel一樣任由心智去建構一個理想圖像呢?
對於部份數學教師而言,教完整數的加減法後,(-5)+3這樣的題目便幾乎不大可能再單獨出現了;負負得正的規則往往也只是一句口訣。但是對於學習者而言,一切真有那麼簡單嗎?也許他們的內心也正如Stendhal一樣正在天人交戰哩!教師是否曾經停駐自己的腳步,傾聽一下學生的聲音呢?當然,也許孩子們只需要一個簡單有趣的「遊戲規則」哩!誰知道?又是怎麼知道?
無論如何,我們大可以放膽試著從歷史實例中「考察認知特徵」,與學生身上所「觀察」到的相互「對照」;畢竟歷史不應該只是供我們做為新課程的話引或課餘的閒聊話題而已。德國數學家與教育家Felix Klein在1908年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現在帶著批判的眼光去看中學裡負數的教法,常常可以發現一個錯誤,就是像老一代數學家如上指出的那樣,努力地去證明記號法則的邏輯必要性。
……我反對這種做法,我請求你們別把不可能的證明講得似乎成立。大家應該用簡單的例子來使學生相信,或有可能的話,讓他們自己弄清楚。
即使是近一世紀後的今天,無論是努力為學生「證明」記號法則還是努力教同學去「背」記號法則的老師,這些話都仍然受用。「會教」的老師讓自己和同學們聽得明白,也會讓自己和同學們想得明白、滿心歡喜。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