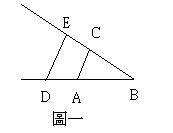 在書寫方式上,笛卡兒用的是友善及直接訴求般迷人的語調,這種語調不像出自數學家反倒像是一位工匠告訴讀者如何製作傢俱:
在書寫方式上,笛卡兒用的是友善及直接訴求般迷人的語調,這種語調不像出自數學家反倒像是一位工匠告訴讀者如何製作傢俱:幾何『修辭』:笛卡兒 vs. 歐幾里得
台師大數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黃清揚
摘譯序
本篇文章摘譯自1988年二月出版的雜誌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中John Fauvel的著作 “Cartesian and Euclidean Rhetoric” (pp. 25-29)。這裡要對『修辭』做個解釋,這一名詞在此特別是指數學文本中的書寫方式,包含語調(法)及文字的使用。而書寫方式的不同就好比不同老師所採用的不同上課方式,有沉悶也有愉悅。作者基於對數學教育的關懷,整合數學史的發展寫下了這篇文章,並給大家深刻的省思。
前言
在日常教學環境中,是否有一種最好的方式來溝通數學?以時間至上的上課模式來說,學習者日復一日的坐在椅子上,看著教師在黑板上書寫的背影,每次五十分鐘,並接受一連串像是輔助定理、定理4.2.1、證明以及備註等等數學知識。這種方式對講課者來說是方便的,學生也易於記憶,缺點則是學生無法察覺數學是可親近的,甚至從開頭便不知所措,失去學習的樂趣。另一種講課方式,老師能激發學生的熱情,引導學生相信數學是一門真正有趣的科目並樂意學習。這種方式雖然留給學生溫暖與快樂的感覺,但是,它的缺點則是未給予學生充分的實質內容來強化這種感覺,或是讓學生誤以為這門課是簡易的,但在自行研讀時,遭遇到極大的困難。
以上所述,也見於各種數學的文本。於此,這裡便是要介紹過去兩種有著高度影響力的著作:300B.C.左右歐幾里得所著的《幾何原本》(The Elements) 與笛卡兒1637年出版的《幾何學》(Geometry)。文章中我將數學的溝通描述為毆幾里得或是笛卡兒『修辭』是根據某一個文本讀起來與看起來比較像《幾何原本》或《幾何學》而定。再說到『修辭』與數學的連結,這裡僅止於關懷語言如何用於溝通數學,一位作者選擇怎樣的寫作方式與來讀者溝通,所呈現出來的『修辭』正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歐幾里得『修辭』
《幾何原本》中『定義-公理-命題-證明』的型式是歐幾里得對上千個相似的產品最終的巧思。我們評估歐幾里得『修辭』,特別有趣的地方是他完全直接的態度:沒有跡象顯示作者曾經注意到讀者的存在,因為在書中他努力地在陳述所謂「永恆的真理」。這種模式已被證明為高度成功的書寫方式,明顯地,故意忽略讀者一直不被視為是不容易理解的。
笛卡兒「修辭」
笛卡兒的《幾何學》提供讀者另一種『作者與讀者』關係的世界。《幾何學》乃是1637年於萊登(Leiden)出版的《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中附於書末三篇論文中之最後一篇。《方法論》中所採用的口吻與《幾何學》是一致的,笛卡兒告訴讀者他提供這本書僅當作是歷史或是虛構的故事。而書中對不同時間的描述有著精細的控制,譬如它包含了『寫作的時間』、『讀者經由文本進展的時間』以及『描述事件的時間』等等。簡而言之,笛卡兒絞盡腦汁來定義及架構讀者的反響,而這也是最成功的策略。
檢視《幾何學》,笛卡兒將所訴求的讀者對象設定在『初學者』,因為他在開宗明義就指出: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試著讓每一個人對我的意思能清楚的了解;但我懷疑是否這篇論文能被不熟悉幾何的讀者來閱讀,因為我已經認為重複在裡面的論述是多餘的。
相較之下,《方法論》中其他的部分則並非如此。我們要特別注意到《幾何學》反而是放在《方法論》最後的地方。由此看來,儘管他使用的是家鄉話以及較愉悅的模式,作者似乎在前提上就認定大多數的讀者不能讀懂他的書。對於當時的同行來說,他的書的確與眾不同,也因為他的書難以了解,我們也可想像笛卡兒如何技巧性的贏得聲名與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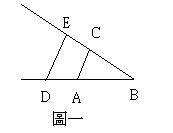 在書寫方式上,笛卡兒用的是友善及直接訴求般迷人的語調,這種語調不像出自數學家反倒像是一位工匠告訴讀者如何製作傢俱:
在書寫方式上,笛卡兒用的是友善及直接訴求般迷人的語調,這種語調不像出自數學家反倒像是一位工匠告訴讀者如何製作傢俱:
假定AB是單位,現在想要將BC乘BD,我只要連接點A與C,然後畫CA的平行線DE,BE即為乘積。(如圖一)
相較於笛卡兒,歐幾里得則採用面積來操作(因為對歐幾里得來說,兩個數或量相乘其結果必須用面積來替代,並且數與量要分開處理),其語調就較為嚴肅,請參見《幾何原本》第七冊定義16:
兩數相乘得出的數稱為面,其兩邊就是相乘的兩數。
有了以上定義之後,接下去他才處理數與量的乘法。
另外,對於讀者來說,笛卡兒體貼地未將數學知識所有細節陳述出來(歐幾里得則否),因為他認為過多的敘述令人感到厭煩,如果將這些刪掉的部份留給讀者自己來發現,或許他們會覺得更有樂趣才是。
最後,笛卡兒相信用這樣的『修辭』方式來縱貫全文,後人會給他仁慈的評斷,事實的確也是如此。
笛卡兒『修辭』的成功
雖然笛卡兒最初的文本曾讓讀者稍稍懷疑他的才華,但經由荷蘭籍拉丁文譯者Frans
van Schooten的努力,卻使它在數學社群中博得好評,並風靡到法國以外的地區。如同Jan
van Maanen曾經指出:笛卡兒的數學能夠普及,大部分的成就要歸功於Frans
van Schooten,並經由此一荷蘭人,《幾何學》成為教育性的文本。
修辭學上的回嚮
綜觀數學史,歐幾里得與笛卡兒『修辭』絕不是數學文本中僅有的兩種書寫方法(英國數學家Robert Record另有一種柏拉圖式的『修辭』風格)。我們在檢視其他人的『修辭』時,也必須面對自己的實務經驗。為了不同的目的(教師或作者),我們應該使用怎樣的「修辭」呢?而這種形式的「修辭」在溝通上又是如何進行?(特別是在課堂上教師如何與學生溝通?)從HPM的觀點來看,企圖回答這些問題,一定可以幫助我們從自身實務經驗跳脫出來,賦予批判性的反思,並且擴及其他可能的領域之學習。